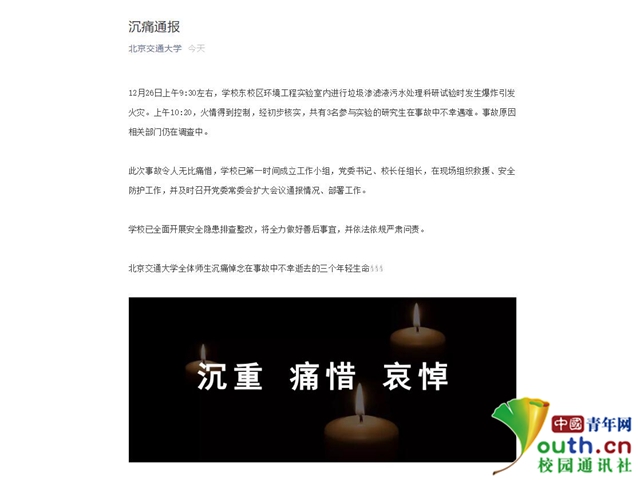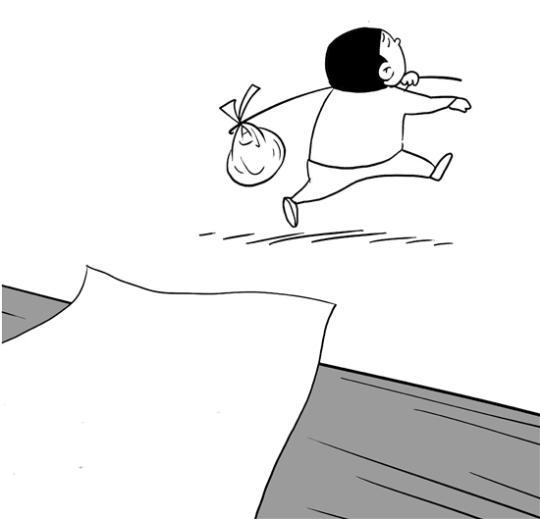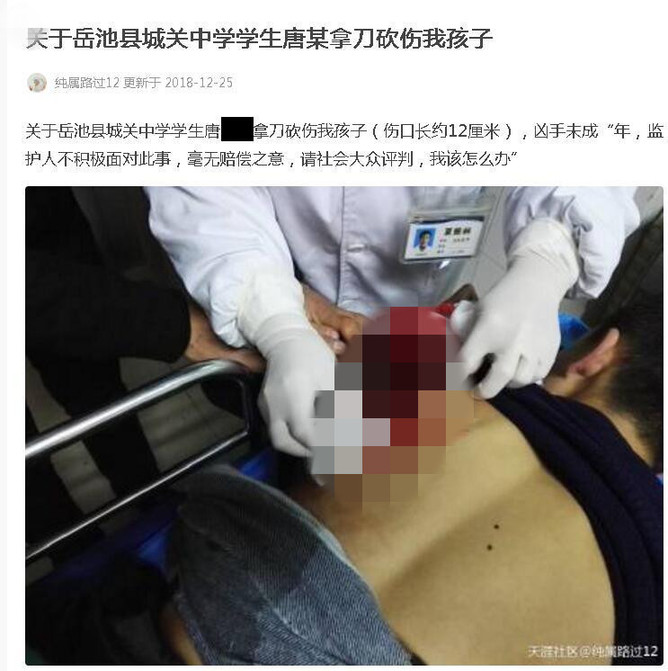гҖҖгҖҖ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йңҖиҰҒдёҖиҠӮз”ҹжӯ»иҜҫ дҪ жҳҜеҗҰжғіиҝҮ究з«ҹиҜҘжҖҺж ·дёҺиҮӘе·ұжҲ–家дәәйҒ“еҲ«пјҹ
гҖҖгҖҖз”ҹе‘Ҫзҡ„е°ҪеӨҙи°ҒеҒҡдё»пјҹеҢ»з”ҹпјҹ家дәәпјҹиҝҳжҳҜиҮӘе·ұпјҹж— и®әеҰӮдҪ•пјҢжүҖжңүдәәйғҪйҒҝдёҚејҖжӯ»дәЎиҝҷ件дәӢжғ…гҖӮз”ҹжҙ»йҮҢпјҢжңүдәәжӯЈз»ҸеҺҶзқҖз—…з—ӣжҠҳзЈЁпјӣжңүдәәжӯЈйқўеҜ№зқҖдәІдәәеҚіе°ҶзҰ»ејҖзҡ„дәӢе®һпјӣжңүдәәдёҚзҹҘйҒ“иҜҘжҖҺд№ҲйқўеҜ№жңҖз»ҲжқҘдёҙзҡ„йӮЈдёҖеҲ»пјҢж„ҹеҲ°жҒҗжғ§е’Ңж— еҠ©гҖӮ
гҖҖгҖҖеәҶе№ёзҡ„жҳҜпјҢеҰӮд»ҠдёҚ少专家гҖҒеӯҰиҖ…д»ҘеҸҠдё“дёҡдәәеЈ«пјҢе·Із»Ҹе…із…§еҲ°дәә们зҡ„йңҖжұӮпјҢе°Ҷз”ҹжӯ»еӯҰиҝҷй—ЁеӯҰй—®еёҰеҲ°еӨ§дј—дёӯй—ҙиҝӣиЎҢдј ж’ӯгҖӮж— и®әжҳҜз”ҹеүҚйў„еҳұиҝҳжҳҜзј“е’ҢеҢ»з–—зҡ„жҰӮеҝөпјҢйғҪе·Із»Ҹж…ўж…ўжёҗе…ҘдәәеҝғгҖӮ
гҖҖгҖҖе°ұеңЁдёӨеӨ©еүҚзҡ„еҶ¬иҮіж—ҘпјҢдёҖеңәе…ідәҺз”ҹжӯ»еӯҰзҡ„е…¬зӣҠи®Іеә§еңЁеҢ—дә¬дёҫеҠһгҖӮдё»еҠһиҖ…еҢ—дә¬еёӮд»ҒзҲұж…Ҳе–„еҹәйҮ‘дјҡйӮҖиҜ·жқҘеҒҡеҲҶдә«зҡ„еҳүе®ҫдёӯпјҢжңүз”ҹеүҚйў„еҳұзҡ„жҺЁе№ҝиҖ…гҖҒеңЁеӨ§еӯҰејҖи®ҫз”ҹжӯ»еӯҰзҡ„ж•ҷжҺҲпјӣжңү80еҗҺйқўеҜ№еҸҢдәІзҰ»дё–зҡ„зӢ¬з”ҹеӯҗеҘіпјӣд№ҹжңүеё®еҠ©жӮЈиҖ…е’Ң家еұһиҝҺжҺҘжңҖеҗҺж—¶еҲ»зҡ„зј“е’ҢеҢ»з–—и·өиЎҢиҖ…вҖҰвҖҰ
гҖҖгҖҖв– 50еІҒдёәиҮӘе·ұеҶҷеҘҪйҒ—еҳұ
гҖҖгҖҖд»Ҡе№ҙ60еӨҡеІҒзҡ„йҷҶжҷ“еЁ…ж•ҷжҺҲпјҢжӣҫз»Ҹд»»иҒҢдәҺгҖҠдёӯеӣҪйқ’е№ҙжҠҘгҖӢпјҢдёҖжүӢејҖеҠһдәҶжңүеҪұе“ҚеҠӣзҡ„вҖңйқ’жҳҘзғӯзәҝвҖқгҖӮ50еІҒеҮәеӨҙзҡ„ж—¶еҖҷпјҢйҷҶжҷ“еЁ…дёәиҮӘе·ұеҶҷеҘҪдәҶдёҖд»ҪйҒ—еҳұпјҢиҝҳеҸ‘з»ҷдәҶдёҚе°‘дәІеҸӢзңӢгҖӮзҺ°еңЁеҚҒеӨҡе№ҙиҝҮеҺ»дәҶпјҢеҘ№жҲҗдёәдёҖеҗҚз”ҹеүҚйў„еҳұзҡ„жҺЁе№ҝиҖ…пјҢиҝҳеңЁеҢ—еёҲеӨ§ејҖи®ҫдәҶдёҖй—ЁгҖҠеҪұеғҸдёӯзҡ„з”ҹжӯ»иҜҫгҖӢгҖӮ
гҖҖгҖҖдёәд»Җд№ҲиҰҒ50еІҒзҡ„ж—¶еҖҷз»ҷиҮӘе·ұеҶҷдёҖд»ҪйҒ—еҳұпјҹе…¬зӣҠиҜҫе ӮдёҠпјҢеҘ№еҲҶдә«дәҶиҮӘе·ұеҶҷйҒ—еҳұзҡ„еҝғи·ҜеҺҶзЁӢгҖӮйӮЈдёҖе№ҙпјҢеҘ№еӨ§еӯҰйҮҢжңҖиҰҒеҘҪзҡ„жңӢеҸӢеҺ»дё–дәҶгҖӮжңӢеҸӢзҡ„еҘіе„ҝеңЁеҰҲеҰҲзҡ„йҒ—зү©йҮҢжүҫ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зӣёзүҮзҡ„еә•зүҮпјҢйӮЈжҳҜеҘ№еҰҲеҰҲдёәиҮӘе·ұзҡ„葬зӨјеҮҶеӨҮзҡ„з…§зүҮгҖӮйҷҶжҷ“еЁ…зҢңжғіпјҢиҝҷдҪҚжңӢеҸӢеҸҜиғҪжІЎжңүеҶҷдёӢйҒ—еҳұпјҢжҲ–иҖ…еңЁдёҙз»Ҳзҡ„ж—¶еҖҷи·ҹеҘ№зҡ„家дәәжңүиҝҮйқһеёёеӨҡзҡ„ж·ұе…Ҙзҡ„дәӨжөҒгҖӮеӣ дёәиҝҷеј з…§зүҮзҡ„дәӢжғ…пјҢеҘ№зҡ„еҘіе„ҝжҳҜеңЁеҘ№еҺ»дё–д»ҘеҗҺжүҚеҸ‘зҺ°зҡ„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и°Ҳи®әжӯ»дәЎпјҢж•ҙдёӘеҚҺдәәж–ҮеҢ–йҮҢеҸҜиғҪйғҪи§үеҫ—жҳҜдёҖдёӘйқһеёёйҡҫд»ҘејҖеҸЈзҡ„дәӢжғ…пјҢжҲ‘зҡ„иҝҷдҪҚжңӢеҸӢзҰ»ејҖд»ҘеҗҺпјҢжҲ‘еҶҷдёӢдәҶиҮӘе·ұзҡ„第дёҖд»ҪйҒ—еҳұгҖӮвҖқйҷҶжҷ“еЁ…иҜҙпјҢеҘ№зҺ°еңЁиҝҳи®°еҫ—пјҢзңҹејҖе§ӢеҠЁз¬”еҶҷйҒ—еҳұж—¶еҖҷпјҢиҝҳжҳҜдјҡи§үеҫ—дёҺдё–з•ҢеҲ«иҝҮйқһеёёең°дёҚиҲҚгҖӮеҪ“еҶҷеҲ°жғіи·ҹ家дәәиҜҙзҡ„иҜқзҡ„ж—¶еҖҷпјҢеҘ№еҝҚдёҚдҪҸжөҒзңјжіӘ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иҝҮдәҶ60еІҒд»ҘеҗҺпјҢеҘ№еҸҲеўһеҠ дәҶдёҖдёӘд»ӘејҸпјҢжҜҸе№ҙзҡ„з”ҹж—ҘиҰҒж”№дёҖйҒҚйҒ—еҳұгҖӮвҖңеҪ“дҪ еӢҮж•ўең°йқўеҜ№жқҘж—Ҙж— еӨҡзҡ„зҺ°е®һж—¶пјҢдҪ жүҚиғҪжӣҙеҘҪең°зҸҚжғңжҜҸдёҖеӨ©пјҢжҙ»еҘҪжҜҸдёҖеӨ©гҖӮдёҺе…¶жӢје‘ҪеҠӘеҠӣеҺ»еўһеҠ з”ҹе‘Ҫзҡ„й•ҝеәҰпјҢдёҚеҰӮеҘҪеҘҪең°ж”№е–„з”ҹе‘Ҫзҡ„иҙЁйҮҸпјҢдёҺе…¶жҠҠиҮӘе·ұжҙ»жҲҗдёӘиЎҢе°ёиө°иӮүпјҢдёҚеҰӮи®©иҮӘе·ұжҙ»зқҖзҡ„жҜҸдёҖеӨ©йғҪеҸҳжҲҗиҠӮж—ҘпјҢеӯҰд№ зҡ„иҠӮж—ҘгҖҒе·ҘдҪңзҡ„иҠӮж—ҘпјҢеҲӣйҖ зҡ„иҠӮж—ҘпјҢжҖқжғізҡ„иҠӮж—ҘгҖҒзҫҺзҡ„иҠӮж—ҘгҖҒзҲұзҡ„иҠӮж—ҘгҖӮвҖқйҷҶжҷ“еЁ…и®ӨдёәпјҢжҸҗеүҚеҜ№жӯ»дәЎжңүи®ӨзҹҘпјҢжүҚиғҪжӣҙеҠ жңүж„Ҹд№үең°жҙ»еҘҪжҜҸдёҖеӨ©гҖӮ
гҖҖгҖҖв– 80еҗҺзӢ¬з”ҹеӯҗеҘіеҰӮдҪ•еә”еҜ№дәІдәәзҰ»еҺ»
гҖҖгҖҖеңЁеҢ»еӯҰдј еӘ’дёҡе·ҘдҪңзҡ„зҮ•е°Ҹе…ӯжҳҜдёҖеҗҚ80еҗҺзӢ¬з”ҹеӯҗеҘіпјҢеңЁз»ҸеҺҶзҲ¶жҜҚе…ҲеҗҺиў«зЎ®иҜҠдёәз»қз—Үж—¶пјҢжүҖжңүзҡ„еҢ»з–—жҠўж•‘еҶіе®ҡйғҪиҰҒеҘ№иҮӘе·ұеҒҡпјҢжүҖжңүз…§йЎҫ家еәӯе’ҢдәІдәәзҡ„жӢ…еӯҗйғҪиҰҒиҮӘе·ұжҢ‘ж—¶пјҢеҘ№жүҚи§үеҫ—иҮӘе·ұжҳҜдёӘе®Ңе…ЁзӢ¬з«Ӣзҡ„жҲҗдәә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зҲ¶жҜҚз”ҹз—…е’ҢзҰ»еҺ»зҡ„йӮЈж®өж—ҘеӯҗйҮҢпјҢеҘ№з»ҸеҺҶдәҶдёҖдёӘдәәз”ҹзҡ„дҪҺжҪ®пјҢйңҖиҰҒеҗ‘жңӢеҸӢеҖҫиҜүпјҢд№ҹжұӮеҠ©дәҶеҝғзҗҶиҲ’зј“жІ»з–—гҖӮеҘ№д№ҹеӯҰдјҡдәҶпјҢе°ҶеҺӢеҠӣеҲҶж•ЈпјҢз”ҹжҙ»дёҠжұӮеҠ©дәҺеҲ«дәәдёәиҮӘе·ұеҮҸиҙҹ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жҲ‘зҺ°еңЁиә«иҫ№зҡ„жңӢеҸӢдјҡиҜҙпјҢжҲ‘зҡ„дёҖдёӘжҜ”иҫғзӘҒеҮәзҡ„дјҳзӮ№е°ұжҳҜзңӢиҮӘе·ұеҘҪзҡ„дёҖйқўпјҢеҺ»зңӢе®ғеҸҜи§ЈеҶізҡ„дёҖйқўпјҢеҺ»жүҫеҲ°и§ЈеҶіж–№жЎҲгҖӮеңЁжҲ‘们зҡ„з”ҹжҙ»еҪ“дёӯпјҢжӯ»дәЎжҳҜеҝ…дјҡеҸ‘з”ҹзҡ„дёҖ件дәӢгҖӮж„ҸеӨ–д№ҹжҳҜдёҖе®ҡдјҡеҲ°жқҘзҡ„дёңиҘҝпјҢжҢ«жҠҳд№ҹжҳҜпјҢзӘҒ然д№ҹжҳҜгҖӮе®ғдёҚдјҡи·ҹжҲ‘们жү“жӢӣе‘јпјҢиҜҙжқҘе°ұжқҘгҖӮ然еҗҺе®ғжқҘдәҶд»ҘеҗҺпјҢеҰӮжһңжҲ‘们иҮӘе·ұеҝғжҖҒеҮҶеӨҮеҘҪпјҢжҲ‘们зҹҘйҒ“е®ғдёҖе®ҡдјҡеҮәзҺ°гҖӮжҲ‘们йҡҸж—¶йғҪжҳҜеҮҶеӨҮзқҖпјҢ然еҗҺз”ЁиҮӘе·ұеҘҪзҡ„дёҖйқўгҖҒз§ҜжһҒзҡ„дёҖйқўеҺ»зңӢиҝҷдёӘз”ҹжҙ»пјҢз”ҹжҙ»е°ұжҳҜеҫҲзҫҺеҘҪзҡ„гҖӮвҖқ
гҖҖгҖҖв– зј“е’ҢеҢ»з–—и®©з”ҹе‘Ҫиө°еҫ—жӣҙд»Һе®№
гҖҖгҖҖжқҘиҮӘеҚҸе’ҢеҢ»йҷўзҡ„е®Ғжҷ“зәўж•ҷжҺҲпјҢжҳҜдёҖеҗҚзј“е’ҢеҢ»з–—зҡ„жҺЁеҠЁиҖ…гҖӮзј“е’ҢеҢ»з–—еҫҲеӨҡдәәйғҪи§үеҫ—йҷҢз”ҹпјҢе…¶е®һе®ғдёҺдёҙз»Ҳе…іжҖҖгҖҒе®үе®Ғз–—жҠӨгҖҒе®Ғе…»з–—жҠӨиҝҷдәӣжҰӮеҝөеҹәжң¬зӣёеҗҢпјҢжҳҜжҢҮеҜ№з”ҹе‘Ҫжңҹжңүйҷҗзҡ„з—…дәәеҸҠ其家еәӯзҡ„з…§йЎҫ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еҚҸе’ҢеҢ»йҷўеӨҡе№ҙзҡ„иЎҢеҢ»дёӯпјҢе®Ғжҷ“зәўи§ҒеҲ°дәҶеӨӘеӨҡзҡ„з”ҹжӯ»пјҢд»ҘеҸҠз—…дәәе’Ң家еұһеңЁжңҖеҗҺж—¶еҲ»зҡ„ж— еҠ©гҖӮеҘ№еҝғйҮҢдёәиҝҷдәӣжӮЈиҖ…е’Ң家еұһж„ҹеҲ°з—ӣиӢҰпјҢеҗҢж—¶д№ҹжғіе°ҪеҠӣеё®еҠ©д»–们гҖӮ2008е№ҙеҘ№еҠ е…ҘдәҶеҢ—дә¬жҠ—зҷҢеҚҸдјҡзҷҢз—Үеә·еӨҚдёҺ姑жҒҜжІ»з–—дё“дёҡ委е‘ҳдјҡпјҢеңЁзҷҢз—ӣжІ»з–—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Ҙ№еҗ¬еҲ°дёҖдёӘиҜҚеҸ«вҖң姑жҒҜжІ»з–—вҖқгҖӮеңЁеҸ°ж№ҫеӯҰд№ иҝҷз§ҚвҖңе®үе®Ғз–—жҠӨвҖқж—¶пјҢеҘ№иў«йңҮж’јеҲ°дәҶпјҡеҺҹжқҘдәәиҝҳеҸҜд»Ҙиҝҷж ·жӯ»вҖ”вҖ”еҢ»йҷўйҮҢдё“й—Ёз»ҷиҝҷдәӣз—…дәәз—…жҲҝпјҢиҝҳжңүеҝ—ж„ҝиҖ…пјҢиҝҳжңүеҺЁжҲҝз”ҡиҮій’ўзҗҙгҖӮзј“е’ҢеҢ»з–—з…§йЎҫеҲ°жӮЈиҖ…е’Ң家дәәвҖңиә«гҖҒеҝғгҖҒзӨҫгҖҒзҒөвҖқеӣӣдёӘеұӮйқўпјҢеҠӣеӣҫеңЁжңҖеӨ§зЁӢеәҰдёҠдҪҝжӮЈиҖ…еңЁдәәз”ҹзҡ„жңҖеҗҺдёҖзЁӢиҝңзҰ»з—ӣиӢҰпјҢжңүе°ҠдёҘең°зҰ»еҺ»гҖӮд»ҺжӯӨеҗҺпјҢеҘ№жҲҗдёәвҖңзј“е’ҢеҢ»з–—вҖқзҡ„жҺЁеҠЁиҖ…пјҢеңЁеҚҸе’ҢеҢ»йҷўиҝӣиЎҢдәҶзј“е’ҢеҢ»з–—зҡ„еӨ§иғҶе°қиҜ•гҖӮ
гҖҖгҖҖз”ҹе‘Ҫжңҹжңүйҷҗзҡ„з—…дәәйҖҡеёёдјҡиў«еҠЁең°жҺҘеҸ—иҝҷж ·зҡ„е®үжҺ’пјҡдёҖжҳҜиҝҮеәҰжІ»з–—пјҢжңүдәӣзӣҙеҲ°з”ҹе‘Ҫзҡ„жңҖеҗҺдёҖеҲ»д»ҚеңЁжҺҘеҸ—еҲӣдјӨжҖ§зҡ„жІ»з–—пјӣдәҢжҳҜжІ»з–—дёҚи¶іпјҢеҸ—еҲ°зҡ„з—ӣиӢҰе’ҢдёҚйҖӮзӣҙеҲ°жӯ»дәЎд№ҹжІЎжңүеҫ—еҲ°е……еҲҶзҡ„и§Ји„ұгҖӮеңЁеҘ№е°қиҜ•зҡ„зј“е’ҢеҢ»з–—дёӯпјҢз—…дәәеҸҜд»ҘеёҰз—…еҺ»ж—…жёёпјҢеҺ»иҮӘе·ұжғіеҺ»зҡ„ең°ж–№пјҢд№ҹжңүжқғеҲ©йҖүжӢ©жҺҘеҸ—ж— еҲӣж— з—ӣиӢҰзҡ„жІ»з–—гҖӮ
гҖҖгҖҖе®Ғжҷ“зәўиҜҙпјҡвҖңеӨ§еӨҡж•°дәә并дёҚжҳҜеҢ»еҠЎдәәе‘ҳпјҢеҜ№дәҺжҲ‘们зҡ„жӯ»дәЎпјҢжҲ‘们家дәәзҡ„жӯ»дәЎиҰҒзҹҘйҒ“зҡ„дёҚи§Ғеҫ—жҜ”еҢ»з”ҹе°‘пјҢжүҖд»ҘжҲ‘们жңүиҰҒжұӮе°ұжҸҗеҮәжқҘпјҢе°ұиҰҒе•ҶйҮҸпјҢдёҚиҰҒи§үеҫ—еҢ»з”ҹиӮҜе®ҡжҜ”жҲ‘зҹҘйҒ“зҡ„еӨҡпјҢеҢ»з”ҹиӮҜе®ҡдјҡе‘ҠиҜүжҲ‘жңҖеҘҪзҡ„зӯ”жЎҲпјҢжҲ‘и§үеҫ—дёҚжҳҜиҝҷж ·зҡ„гҖӮжүҖд»ҘжҲ‘们дёҖиө·еҺ»жҠҠиҝҷ件дәӢжғ…еҒҡеҘҪпјҢдёҖиө·пјҢжҲ‘и§үеҫ—дҪңдёәеҢ»з”ҹд№ҹйңҖиҰҒжқҘиҮӘжӮЈиҖ…е’Ң家дәәзҡ„дҝЎд»»е’Ңйј“еҠұпјҢз”ҡиҮідёҖиө·жғіеҠһжі•пјҢжүҚиғҪеҒҡеҫ—жңҖеҘҪгҖӮвҖқ
гҖҖгҖҖжң¬жҠҘи®°иҖ… еӮ…жҙӢ J004гҖ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