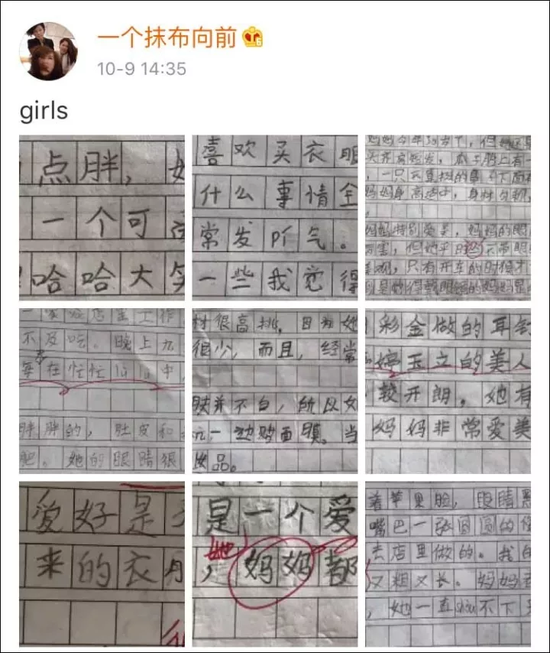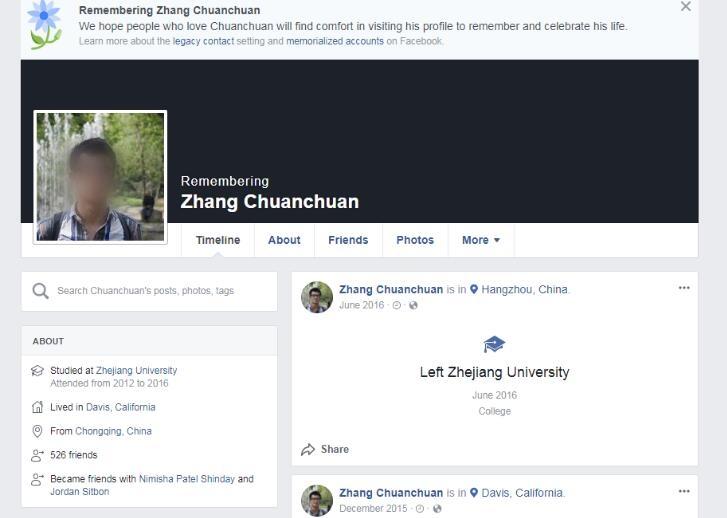阿富汗男孩瓦希德,家住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性格腼腆,长相秀气。
他发现,学校里的一位男老师很喜欢自己。放学后老师常带他去市里的集市,给他买些小玩意,后来甚至送给了他一部手机。
有一天,老师将瓦希德带到一间私人房子里,用瓦希德意料不到的方式,侵犯了他。年幼的瓦希德不堪忍受变态的骚扰和折磨,最终鼓起勇气揭发。
学校得知后,只是开除了这位男老师。

来自英国的一名独立摄影师,在他关于阿富汗的纪实里记录了另外一件事:
他去美军驻守地,跟随十几名军事顾问“巡视”,事实上,当地的治安掌握在当地警察手里。一名美军顾问在警局发现一名腿上有伤的男孩。男孩向他控诉自己受到性侵犯,在试图逃跑时被打伤。
当美军顾问要求警长作出解释并逮捕涉案人,警长满脸不屑地说,“这些男孩是自愿的。再说了,没有男孩,你让我的小伙子们晚上干嘛?”
阿富汗社会情况的确极端,但即便是在宗教礼法极其严苛的背景下,对儿童的性侵犯仍十分普遍。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执行理事穆罕默德·穆萨总结说:“愚昧、教育缺位、法治缺失和贫穷,会让孩子们处境十分艰难。”
一个性教育几乎为零的国家,却有着全世界几乎最高的性犯罪率,特别是针对儿童的。
但性教育的普及,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刻,还要对抗来自成人世界的误解。
还记得吗,只是半年多以前,中国新出的一套性教材曾引起巨大争议,因为有些家长觉得插画中直接出现性器官实在太“污”……

“但性教育本身应该是一个‘去污’的过程。”在一次关于国外性教育问题的采访中,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Mathias Lafolie(中文名:马福力)对记者说。
在性教育这个问题上,阿富汗和瑞典,被比作坐标轴的两端。
瑞典人以他们的性教育走在世界前列而自豪:瑞典学校开始性教育的时间已经提前到了小学一年级,有些家长甚至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告诉他们精子和卵子是如何相遇的——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开始问爸爸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不应该在谈到自己身体或器官的时候感到尴尬,”同时接受采访的瑞典驻华使馆新闻参赞Gabriella Augustsson(中文名:欧瑞雅)拿出一本插画书说,“这就是我给我孩子讲性知识的一本书,在他们上小学之前。”

欧瑞雅是3个孩子的妈妈。她拿出的这本书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版,直译叫“爱之书”。这更像是一本心理学教材,十几页翻过,没有任何“涉性”的插画和语句,只是以渐进、平滑地方式告诉孩子:
“爱是一种感觉,可以是对一株花,也可以是对两条鱼;可以是对某个偶像歌手,也可以是对一块草莓蛋糕……”
一直讲到“相爱的人会举行婚礼,会戴上相似的戒指,会纹上呼应的刺青,会在一起……”
性器官和性行为的插图在此时出现,不避讳,不遮掩。书里接着讲,精子们比着赛向前游,而卵子只会接受最终的胜利者,它们开始一起变成宝宝……
“当然我们会明确地告诉孩子,大人与孩子的行为是有区别的,只有大人的身体才会生孩子,”欧瑞雅说,“但是只有当家长大大方方地告诉孩子,人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人是怎么诞生的,孩子才不会觉得谈论性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
对于如何教孩子预防性侵犯的问题。除了告诉孩子学会说“不”,马福力提醒我,对儿童的性侵犯正呈现越来越多的形式,比如角色扮演。
“很多性侵犯都是从‘来,我们一起做个游戏’开始的。”
只是很多时候,对儿童性侵犯危害缺乏警觉,对性教育缺乏了解和重视的人,并不是我们的孩子。
即便是在日本,一个一贯被认为性文化较为开放的国家,对于性教科书的态度也显得有些暧昧和复杂。

2002年,日本母子卫生研究会曾编写出版一本针对中小学学生的性教育教科书《青春期的爱与身体之书》。
由于书中详细讲述了避开性侵犯和性虐待的方法,该书在发放一个月后即遭多名众议院女议员的抗议,引起国会激烈讨论,最终被认为传播“过激的性教育”而成为绝版。
在部分议员乃至政府高层的强烈抵制下,日本文部省在“新学习指导要领”里明文规定,中(初中)小学保健课性教育“不涉及受精之前的内容”。孩子们要了解这些,只能通过家庭或者教科书之外的学习。
2013年,日本某电视台播出了一部时长48分钟、有关性教育思辨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但视频中讲课的大人,并非是老师,而是普通日本妈妈自发组织起来的小团体。她们自己绘制图片、制作道具、和学校交涉,才有了这样生动的课程。
按照国际上对“全面的、有效的性教育”的定义,性教育的内涵应该包括:性与生殖健康、性别、性行为、情感与关系、价值观念、社交技能、人权等多个方面。
仅仅知道怀孕分娩是怎么回事,绝非是性教育的全部。怎样学会尊重与保护自己和他人,了解其中包含的责任与义务,都是深厚而复杂的学问。
这些,都需要学校、社会和家长共同努力。
(原题为:《当性侵正威胁我们的孩子,性教育却要对抗成人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