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头岛回趟家不容易。
首先要坐车到桂山岛,然后乘轮渡至珠海市,再转乘汽车、高铁或飞机往家赶。
这样一段辗转曲折的路,贺朝阳走了十年。
从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到深中通道项目,十年间,他见证了伶仃洋上的这座孤岛从一片荒芜到世界最大的沉管预制厂的整个过程,参与了两个“世纪工程”的建设。而他自己,也由满头黑发的“小贺”变成了“老贺”。

贺朝阳正在沟通协调工作。中国青年网记者 叶婉莹 摄
2009年贺朝阳第一次上岛,那个时候的牛头岛远没有今天的生机与活力,岛上矿石遍布、杂草丛生、渺无人烟。他一开始是有点不情愿的,“但既然来了,就得把这份工作做好,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和操守。”
面对“一穷二白”的岛屿,贺朝阳几乎从零开始干起。联系相关施工单位和业主,与海事等有关单位沟通,奔波于各部门间协调……一切都在他的运作下井井有条。
经过一年多的鏖战,荒芜的孤岛上终于有了宿舍楼,办公楼,饭堂等基本生活设施,为中交四航局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部的后续“进驻”打下基础。
“首先得把大家的吃喝拉撒问题给解决了,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怎么能干好工程呢?我必须要给咱们的建设者搞好后勤工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贺朝阳说。
作为第一批港珠澳大桥大桥岛隧建设者,张文森首次上岛时的心情也并不轻松。没水没电没道路没通讯信号,与世隔绝的荒凉感是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刚上岛的时候正好是夏季,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来到施工现场,背着个工具包,里面放着本图纸,再加上一个军用水壶,在施工现场一待就是一整天。”张文森说,因为要赶工期,许多人经常待到半夜才回去休息。
白天的时候,岛上日光强烈,又没有遮阴的地方,中午也只能顶着个大太阳在施工现场躺着眯一会儿。“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脱下安全帽之后,帽带遮盖的位置特别白。”张文森说,“不是因为大家皮肤白,而是其它部分都晒得很黑,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作中的张文森(右一)。受访者供图
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张文森和他的同事们仅用14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沉管预制厂,在浩渺的伶仃洋上构筑出一座占地56万平方米的“世纪梦工厂”,保证了港珠澳大桥岛隧沉管的供给。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庞大的一个预制厂的建设工作,我们自己也很震惊。”张文森说,“内心特别自豪,前面所吃的苦都不算什么了,因为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港珠澳大桥能否建成,关键看“岛隧”,“岛隧”能否成功,看“沉管”。而牛头岛上这座庞大的预制厂正是为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提供沉管预制生产服务的。
“我们的沉管最深处在海底45米,需要承受45米的水压,要保证它们在海底滴水不漏,在生产沉管时混凝土浇筑的浇筑十分关键。”周林回忆到,80厘米宽的钢筋笼,内部空间只有40-50厘米,浇筑时四周模板是封闭的,温度高达40多度,又闷又热。而为了保证浇筑质量,他每回都带头钻到钢筋笼内指导和监督混凝土布料及振捣情况。
不畏艰辛、刻苦钻研,把精益求精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人、用到每一道工序。经过六年奋战,他们最终生产出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所需的全部33节超级沉管,创造了海底沉管滴水不漏的奇迹。

在沉管预制厂内的周林。中国青年网记者 叶婉莹 摄
“当我们看到这种结果、看到这种效果的时候,都会觉得每次进到钢筋笼里是值得的!”周林骄傲地说道。
这些生产出的沉管每节长180米,重达80000吨,创造了单个沉管体量最大的世界纪录,要把它们顺利地从陆地转移到水下进行安装,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每节沉管浮在水中时的排水量约75000吨,而‘辽宁号’航母满载时的排水量也只有67500吨。”张文森说,“太重了,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起重设备能把这些管节吊起来。”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应用顶推和深浅坞浮运等科学方法进行操作。每次浅坞区灌水环节都持续70多个小时,员工们要时刻蹲守现场,检查沉管是否存在渗漏,观察和监测坞区结构的稳定性。
“尤其是在坞门止水结构上,哪怕一点点破坏,就会发生类似于水坝坍塌的现象,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为了保障灌水顺利进行,他们一刻也不敢松懈。困了、累了就坐在石头上眯一会儿,饿了就拿一块面包啃一啃,持续奋战三天三夜,才顺利地把管节从陆地转移到水下。
除了技术难题,这群建设者们还要时刻面临来自于大自然的考验。由于牛头岛位于海上,台风对这些身经百战的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2014年超强台风“海鸥”席卷的时候,风力最高达到了12级,E14管节的缆绳被生生扯断,随着风的拉力和海浪的推力,随时可能撞向旁边的E15管节。
时任设备部长的李海峰立即安排人员准备随时更换缆绳。但当时风大浪急,缆绳交错,情况危急,他没有多想,扛起身旁的缆绳就猛地扎进了风急浪涌的海里,向着E14管节的缆桩游去,和其他工友合力完成了深坞内3节沉管16条缆绳的加固工作,保障了沉管的安全。

工作中的李海峰。受访者供图
“当时浪特别大,游的过程中海浪咣当咣当地砸来,呛了很多水,还好最后游过去了。”李海峰说,“事后想想还是有些后怕,但我不后悔。因为如果两个管节真的撞到一起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整个后续施工的影响都非常大。我跳下去了,把沉管的安全给保障了,这就够了,值了!”
但这一切的艰难和困苦,他们很少跟家人提及。
岛上信号本就不好。李海峰还记得刚来那会儿,每天下班之后都要往半山腰爬才能给女朋友打电话。结束一天忙碌工作后的张文森也总是举着手机在岛上四处找信号,看着视频里出现的一双儿女脸上乐开了花。无法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陪伴其左右,一直是他心里的疙瘩。
那条辗转曲折的路贺朝阳走的次数其实并不多的。十年间,他连除夕都有半数是在岛上度过的,女儿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等人生中重要的环节他都是缺席的。有时候偶尔回去一次也只能待个三四天,妻子吐槽他回家像是住宾馆。
内心不是没有遗憾的,但贺朝阳从未后悔。2013年的时候他在岛上入了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么艰辛或者做了多大牺牲,这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贺朝阳说。

张文森和家人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我们从事交建行业,要天南海北地跑,没有办法一直陪伴在家人身边,说没有遗憾是假的。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接受它的性质,如果没有人愿意做,那谁去进行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何有更宽阔的道路能走,有更便捷的桥梁缩短地区间的距离?现在我每次看到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内心都特别自豪,因为那是我流过汗付出过心血的地方。”说到此处,张文森顿了顿,“我希望等以后我的孩子长大了,有一天看到爸爸曾经参建的这些工程,能够为祖国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他的汗水和足迹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国青年网记者 叶婉莹 实习生 宋仕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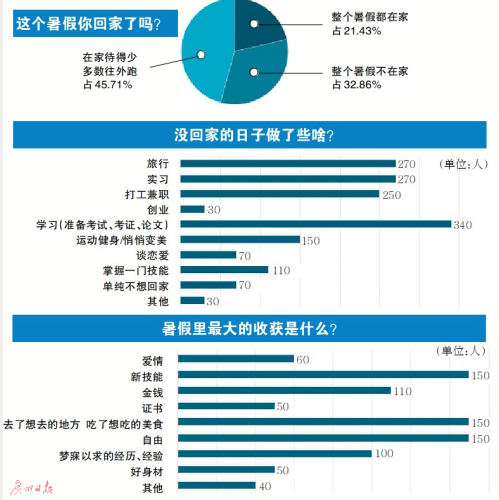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