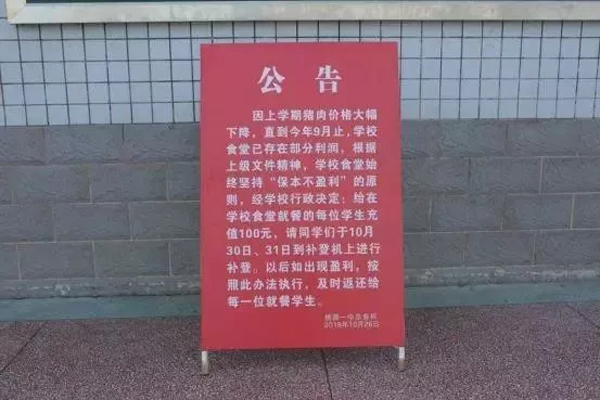гҖҖгҖҖе®үж¬ЎеҢәе…¬е®үе№ІиӯҰвҖңжү“дј вҖқзҺ°еңәгҖӮиҙҫиҝһж–Ң/дҫӣеӣҫ
гҖҖгҖҖеңЁжұҹиҘҝдёҖжүҖеёҲиҢғйҷўж ЎпјҢйҷҲжҳҺйңһеӯҰзҡ„жҳҜеҝғзҗҶеӯҰгҖӮеҺҹжң¬еҘ№зҡ„дәәз”ҹ规еҲ’жҳҜпјҡеҪ“иҖҒеёҲпјҢз»“е©ҡпјҢз”ҹеӯҗгҖӮ
гҖҖгҖҖдёҖеҲҮиў«дёҖж¬ЎвҖңж—…жёёвҖқжү“ж–ӯдәҶгҖӮ2014е№ҙпјҢдёҖеҗҚеҗҢд№ЎеҘҪеҸӢйӮҖиҜ·йҷҲжҳҺйңһеҲ°еҢ—дә¬жёёзҺ©пјҢдҪҶеҪ“и·ҜиҝҮи·қеҢ—дә¬иҝҳжңү50е…¬йҮҢзҡ„жІіеҢ—зңҒе»ҠеқҠеёӮж—¶пјҢеҘҪеҸӢеҚҙиҜҙе·ІеҲ°еҢ—дә¬йғҠеҢәдәҶгҖӮдёӢиҪҰд№ӢеҗҺпјҢеҘ№иў«еёҰеҲ°дёҖеӨ„еҶң家йҷўпјҢд»ҺжӯӨдёҖдёӘеҗҚеҸ«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зҡ„дј й”Җз»„з»Үй—Ҝе…ҘдәҶеҘ№зҡ„з”ҹжҙ»пјҢеҘ№еҗҺжқҘеҲҷжҲҗдёәиҜҘз»„з»Үзҡ„й«ҳеұӮйўҶеҜј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дёәд»Җд№ҲеҪ“еҲқеҘ№иҰҒеҸ«жҲ‘жқҘпјҢдёәд»Җд№ҲиҰҒжҠҠжҲ‘йӘ—иҝӣеҺ»пјҹвҖқеҲҡеҲ°иҖҢз«Ӣд№Ӣе№ҙзҡ„йҷҲжҳҺйңһе“ӯдәҶгҖӮеҘ№еҜ№дёӯеӣҪйқ’е№ҙжҠҘВ·дёӯйқ’еңЁзәҝи®°иҖ…иҜҙпјҢзӣҙеҲ°зҺ°еңЁпјҢиҮӘе·ұйғҪжІЎеҲ°еҢ—дә¬зңӢиҝҮгҖӮ
гҖҖгҖҖеҢ…жӢ¬йҷҲжҳҺйңһеңЁеҶ…пјҢд»Ҡе№ҙ12жңҲ4ж—ҘпјҢ4еҗҚиў«е‘Ҡдәәиў«е»ҠеқҠеёӮе®үж¬ЎеҢәдәәж°‘жі•йҷўдёҖе®ЎеҲҶеҲ«и®Өе®ҡзҠҜз»„з»ҮгҖҒйўҶеҜјдј й”Җжҙ»еҠЁзҪӘпјҢйқһжі•жӢҳзҰҒзҪӘзӯү3йЎ№зҪӘеҗҚпјҢиҺ·еҲ‘3иҮі8е№ҙдёҚзӯүгҖӮ
гҖҖгҖҖ4еҗҚиў«е‘ҠдәәжЎҲеҸ‘пјҢжҳҜз”ұ2017е№ҙзҡ„дёҖиө·е‘ҪжЎҲзүөеҮәзҡ„гҖӮеҪјж—¶пјҢдёҖеҗҚйӮұ姓еӨ§еӯҰз”ҹиҜҜе…Ҙ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дј й”Җз»„з»ҮпјҢеңЁдј й”Җз»„з»ҮзӘқзӮ№пјҢд»–иў«е…¶д»–жҲҗе‘ҳејәеҲ¶зҒҢж°ҙд№ӢеҗҺжӯ»дәЎгҖӮж”ҝжі•жңәе…із«ӢеҚіжҹҘеӨ„пјҢ并еҜ№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з»„з»ҮеҶҚж¬ЎеҪ»жҹҘпјҢиҝҷ4еҗҚиў«е‘ҠдәәпјҢе°ұжҳҜжӯӨж¬ЎеҪ»жҹҘдёӯиў«еҸ‘зҺ°зҡ„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е®үж¬ЎеҢәеӨҡеҗҚеҸ—и®ҝе№ІиӯҰзңӢжқҘпјҢз”ұдәҺиҜҒжҚ®и®Өе®ҡеӣ°йҡҫпјҢз»„з»ҮгҖҒйўҶеҜјдј й”Җжҙ»еҠЁзҪӘиҝҮеҺ»10е№ҙеҮ ж— йҖӮз”ЁпјҢз®—жҳҜвҖңжІүзқЎвҖқзҡ„зҪӘеҗҚпјҢжӯӨз•ӘеҪ“ең°ж”№иҝӣе·ҘдҪңж–№жі•пјҢеҮҶзЎ®йҖӮз”ЁдәҶжі•еҫӢпјҢжҲ–жҳҜжү“еҮ»дј й”Җзҡ„дёҖж¬ЎзӘҒз ҙ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жқҖзҶҹвҖқзҡ„йқһжі•з”ҹж„Ҹ
гҖҖгҖҖеңЁдј й”Җз»„з»Үзҡ„вҖңйўҶеҜјеұӮвҖқйҮҢпјҢ26еІҒзҡ„жҪҳжҳҺжҳҺжҳҜдёӘвҖңејӮзұ»вҖқпјҡеӨ§еӨҡж•°дәәжҳҜжұҹиҘҝиҖҒд№ЎпјҢеҸӘжңүд»–жқҘиҮӘжұҹиӢҸгҖӮиҝҷи®©д»–еңЁеҲҶй…ҚдҪ“зі»дёӯеӨҡе°‘жңүдәӣеҗғдәҸгҖӮ
гҖҖгҖҖдҪңдёәеӣҪеҶ…вҖңиҖҒзүҢвҖқзҡ„дј й”Җз»„з»ҮпјҢ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е§ӢдәҺ2005е№ҙпјҢеңЁе…ЁеӣҪеӨҡдёӘзңҒд»ҪеқҮжңүеҲҶеёғгҖӮдј й”Җдәәе‘ҳйңҖиҰҒиҙӯд№°жҲ–и®©д»–дәәиҙӯд№°е…¶е®һ并дёҚеӯҳеңЁзҡ„вҖңеҢ–еҰҶе“ҒвҖқпјҢжүҚиғҪжҸҗеҚҮиҮӘе·ұзҡ„зӯүзә§пјҢ并且пјҢжӢүжқҘзҡ„дёӢзәҝи¶ҠеӨҡпјҢиҮӘе·ұи®Ўй…¬гҖҒиҝ”еҲ©зҡ„жҜ”дҫӢд№ҹи¶ҠеӨҡ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Ҹ‘иҙўжўҰвҖқзңӢдјјеҫҲзҫҺпјҢдҪҶеңЁеӣҪ家жңүе…ійғЁй—Ёи®Өе®ҡзҡ„дј й”ҖеҗҚеҚ•дёӯпјҢ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жҰңдёҠжңүеҗҚгҖӮ
гҖҖгҖҖе®үж¬ЎеҢәз»ҸдҫҰеӨ§йҳҹеҠһжЎҲж°‘иӯҰиӮ–йҒҘд»Ӣз»ҚпјҢе®үж¬ЎеҢәзҡ„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дј й”Җз»„з»ҮпјҢзӯүзә§д»ҺдҪҺиҮій«ҳеҲҶеҲ«дёәдјҡе‘ҳгҖҒжҺЁе№ҝе‘ҳгҖҒеҹ№и®ӯе‘ҳгҖҒд»ЈзҗҶе‘ҳгҖҒд»ЈзҗҶе•ҶпјҢжҪҳжҳҺжҳҺеұһдәҺд»ЈзҗҶе‘ҳпјҢжҳҜз»„з»Үдёӯзҡ„вҖңдәҢзә§еӨҙзӣ®вҖқпјҢз®—жҳҜй«ҳеұӮ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зҡ„вҖңеҢ–еҰҶе“ҒвҖқеҚ•д»·2900е…ғпјҢжүҖжңү收е…ҘжңҖз»ҲйғҪдјҡжұҮе…ҘвҖңдёҖзә§еӨҙзӣ®вҖқд»ЈзҗҶе•ҶжүӢдёӯгҖӮд№ӢеҗҺпјҢвҖңдёҖзә§еӨҙзӣ®вҖқеҶіе®ҡвҖңдәҢзә§еӨҙзӣ®вҖқеҲҶеҫ—еӨҡе°‘й’ұпјҢд»ҘжӯӨзұ»жҺЁгҖӮиҝҷж„Ҹе‘ізқҖпјҢдёҺдёҠзә§е…ізі»и¶ҠдәІпјҢеҲ°жүӢзҡ„й’ұеҸҜиғҪи¶ҠеӨҡпјҢз”ҡиҮі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жҳҜиҖҒд№ЎпјҢйғҪеҸҜиғҪжІЎжңәдјҡеҪ“вҖңйўҶеҜј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ёҚд»…еҰӮжӯӨпјҢеҗёзәіж–°дәәд№ҹеёёд»ҺиҖҒд№ЎгҖҒеҗҢеӯҰзӯүзҶҹдәәдёӢжүӢгҖӮж°‘иӯҰеҜ№дёӯеӣҪйқ’е№ҙжҠҘВ·дёӯйқ’еңЁзәҝи®°иҖ…дёҫдҫӢпјҢеҗҢдёәвҖңдәҢзә§еӨҙзӣ®вҖқзҡ„еҗҙзҷҫжңүе°ұжҳҜеҸҰдёҖеҗҚж¶үжЎҲвҖңдёҖзә§еӨҙзӣ®вҖқзҡ„иҖҒд№ЎпјҢжӣҙжҳҜй«ҳдёӯж ЎеҸӢгҖӮ
гҖҖгҖҖжҜҸдёӘдәәиҝӣе…Ҙдј й”Җз»„з»Үзҡ„зјҳз”ұеҗ„дёҚзӣёеҗҢгҖӮи®°иҖ…жўізҗҶеҸ‘зҺ°пјҢиҝҷдәӣзјҳз”ұдё»иҰҒеҢ…жӢ¬жҒӢзҲұгҖҒж—…жёёгҖҒжұӮиҒҢдёүз§ҚгҖӮдёҺйҷҲжҳҺйңһдёҖж ·пјҢеҗҙзҷҫжңүиҜҜе…Ҙдј й”Җзҡ„иө·еӣ д№ҹжҳҜеҸ—йӮҖж—…жёёгҖӮ
гҖҖгҖҖ1989е№ҙеҮәз”ҹзҡ„еҗҙзҷҫжңүжң¬з§‘жҜ•дёҡпјҢиә«жқҗж¶ҲзҳҰгҖӮеҺҹе…Ҳд»–еңЁеӨ–ең°жү“е·ҘпјҢ2016е№ҙдёӢеҚҠе№ҙеңЁеә”йӮҖиөҙдә¬жёёзҺ©зҡ„и·ҜдёҠпјҢдёҖеҗҚиҖҒд№Ўз§°е»ҠеқҠи·қеҢ—дә¬иҫғиҝ‘пјҢдҫҝиҜҙжңҚд»–е…ҲеңЁе»ҠеқҠжӯҮдёҖжҷҡгҖӮд№ӢеҗҺд»–иў«еёҰеҲ°дәҶдҪҚдәҺе®үж¬ЎеҢәжқЁзЁҺеҠЎд№Ўзҡ„дёҖеӨ„еҮәз§ҹеҶң家йҷўгҖӮ
гҖҖгҖҖеҶң家йҷўжҳҜдј й”Җз»„з»ҮжңҖе°Ҹзҡ„еҚ•дҪҚпјҢйҖҡеёёз§°дҪңвҖң家вҖқжҲ–иҖ…вҖңеҜқе®ӨвҖқгҖӮж…ўж…ўең°пјҢеҗҙзҷҫжңүеҚҮдёәеҜқе®Өй•ҝпјҢи·»иә«дј й”Җз»„з»Үзҡ„вҖңдёүзә§еӨҙзӣ®вҖқпјҢйҡҸеҗҺжҲҗдәҶз®ЎзҗҶеӨҡдёӘеҜқе®Өй•ҝзҡ„вҖңдәҢзә§еӨҙзӣ®вҖқгҖӮиҝҷдёӘзә§еҲ«зҡ„д»Јд»·пјҢжҳҜд»–жҠ•е…ҘдәҶеӨ§йҮҸйҮ‘й’ұгҖӮ
гҖҖгҖҖе®үж¬ЎеҢәжЈҖеҜҹйҷўеҠһжЎҲжЈҖеҜҹе®ҳжҖ»з»“иҜҙпјҢдёҚе°‘дј й”Җз»„з»ҮжҲҗе‘ҳвҖңжқҘзҡ„ж—¶еҖҷйғҪжҳҜеҸ—е®ідәәвҖқпјҢдҪҶжңүзҡ„еҸ—е®ідәҶжғійҖғзҰ»пјҢжңүзҡ„еҚҙеҠ е…Ҙ并еңЁз»„з»ҮйҮҢеҸ‘еұ•еҲ°дәҶдёҖе®ҡзә§еҲ«гҖӮ
гҖҖгҖҖж–°дәәжғійҖғзҰ»з»„з»Үе…¶е®һеҫҲйҡҫгҖӮиӮ–йҒҘеҲҶжһҗпјҢиҝҷдәӣеҶң家йҷўдҪҚдәҺйғҠеҢәжҲ–еҹҺдёӯжқ‘пјҢдёҖиҲ¬иҖҢиЁҖпјҢеӨ–жқҘжү“е·Ҙдәәе‘ҳиҫғеӨҡпјҢеӣӣе‘ЁжҳҜжөҒеҠЁзҡ„еҮәз§ҹеұӢгҖҒйғҠеҢәгҖҒе·ҘдёҡеҢәпјҢйҷ„иҝ‘жІЎжңүе…¬дәӨиҪҰпјҢвҖңдёҖж—Ұиҝӣе…ҘпјҢж–°жҲҗе‘ҳеҫҲйҡҫд»ҺзӘқзӮ№йҮҢйҖғи·‘пјҢи·‘дәҶд№ҹеҫҲе®№жҳ“иў«жҠ“еӣһжқҘ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еӨҡеҗҚж”ҝжі•е№ІиӯҰйҖҸйңІпјҢиҜҜе…ҘжӯӨең°зҡ„е№ҙиҪ»дәәпјҢдё»иҰҒжҳҜ1990е№ҙеүҚеҗҺеҮәз”ҹзҡ„еӨ§еӯҰжҜ•дёҡз”ҹпјҢз”ҡиҮіжңүзҡ„жқҘиҮӘеҢ—дә¬гҖҒйҷ•иҘҝзӯүең°и‘—еҗҚй«ҳж ЎгҖӮ
гҖҖгҖҖеҗғйҰ’еӨҙиҰҒиҜҙеңЁеҗғйІҚйұј
гҖҖгҖҖеңЁ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дј й”Җз»„з»ҮйҮҢпјҢе№ҙиҪ»дәәдјҡз»ҸеҺҶд»Җд№ҲпјҹеӨҡеҗҚеҠһжЎҲдәәе‘ҳе‘ҠиҜүдёӯеӣҪйқ’е№ҙжҠҘВ·дёӯйқ’еңЁзәҝи®°иҖ…пјҢиҜҘз»„з»ҮйҮҢзҡ„第дёҖиҜҫжҳҜвҖңжҙ—и„‘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ёҖеҗҚеҠһжЎҲдәәе‘ҳиҜҙпјҢж–°дәәе…Ҳдјҡиў«иҰҒжұӮеңЁвҖңиҜҫе ӮвҖқдёҠжң—иҜ»жҲҗеҠҹеӯҰд№ҰзұҚпјҢз”ҡиҮіиғҢиҜөдёҠиҜҫеҶ…е®№гҖӮдёӢиҜҫеҗҺпјҢж–°жҲҗе‘ҳеӣһеҲ°еҜқе®ӨпјҢиҖҢеҜқе®ӨйҮҢйҖҡеёёйҷӨдәҶд»–д№ӢеӨ–еҮ д№Һе…ЁжҳҜиў«жҙ—и„‘жҲҗеҠҹзҡ„иҖҒжҲҗе‘ҳпјҢвҖңиҖҒжҲҗе‘ҳдјҡвҖҳзӣ‘зқЈвҖҷж–°жҲҗе‘ҳзҡ„жҙ—и„‘зЁӢеәҰпјҢзӯүеҲ°ж–°жҲҗе‘ҳвҖҳжҖқжғізЁіе®ҡвҖҷдәҶпјҢе®Ҳ规зҹ©дәҶпјҢжүҚиғҪи®©д»–дёҺе…¶д»–ж–°жҲҗе‘ҳдҪҸеңЁдёҖиө·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еҜқе®ӨйҖҡеёёжҳҜ15~30дәәпјҢз”·еҘіж··дҪҸпјҢжқЎд»¶иү°иӢҰгҖӮжҷ®йҖҡжҲҗе‘ҳйҖҡеёёиәәеңЁеЎ‘ж–ҷжіЎжІ«жқҝдёҠпјҢжңүж—¶пјҢжҢ‘зқҖеҮҢжҷЁжҲ–жҷҡдёҠпјҢ他们иҝҳиҰҒжҠұзқҖвҖңеәҠй“әвҖқеҲ°еә„зЁјең°йҮҢзқЎи§үпјҢеҺ»ж ‘жһ—гҖҒйҮҺең°дёҠиҜҫгҖӮз»„з»ҮйҮҢжҠҠиҝҷз§ҚиЎҢеҠЁеҸ«вҖңжӢүз»ғ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з”ұдәҺеҮәиЎҢвҖңжҳјдјҸеӨңеҮәвҖқпјҢиҝҮеҺ»дёҖж®өж—¶й—ҙпјҢеҫҲе°‘жңүжқ‘ж°‘з•ҷж„ҸиҝҮиҝҷжү№е№ҙиҪ»дәәзҡ„еӯҳеңЁ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Ҹ‘иҙўеҸ‘иҙўеҸ‘иҙўвҖқиҝҷж ·йҮҚеӨҚзҡ„еҸЈеҸ·жҲҗдёәз”ҹжҙ»еёёжҖҒпјҢз”ҡиҮіпјҢиҝһеҗғйҘӯе–қж°ҙд№ҹдёҺеҸ‘иҙўиҒ”зі»еңЁдәҶдёҖиө·гҖӮ
гҖҖгҖҖд»ӨеҠһжЎҲдәәе‘ҳеҚ°иұЎж·ұеҲ»зҡ„жҳҜпјҢжңүдј й”ҖжҲҗе‘ҳеҸҚжҳ пјҢ他们е–қзҡ„жҳҺжҳҺжҳҜзҷҪејҖж°ҙпјҢеҚҙиў«иҰҒжұӮеӨ§еЈ°иҜҙиҮӘе·ұе–қзҡ„жҳҜдә”зІ®ж¶ІпјҢжҳҺжҳҺеңЁеҗғйҰ’еӨҙпјҢдёҠзә§еҚҙиҰҒжұӮ他们и®ӨдёәиҮӘе·ұеңЁеҗғзҮ•зӘқйІҚйұј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Ө§е®¶е…ізі»жҢәвҖҳиһҚжҙҪвҖҷзҡ„гҖӮвҖқеҗҙзҷҫжңүеҜ№и®°иҖ…иҜҙпјҢеҶң家йҷўйҮҢеӨҡжҳҜиҖҒд№ЎпјҢжҖ»жңүдәәжүҫд»–иҒҠеӨ©гҖӮйҷҲжҳҺйңһд№ҹзңӢеҲ°пјҢиҝҷйҮҢдёҖзҫӨе№ҙиҪ»дәәдёҖиө·зҺ©пјҢ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зү№еҲ«жңүжҝҖжғ…пјҢеӣ иҖҢеҘ№д№ҹжңӘиҝҮеӨҡйҳІеӨҮгҖӮ
гҖҖгҖҖиӢҘжңүдёҚжңҚж°”зҡ„пјҢжңүзҡ„жҲҗе‘ҳеҲҷдјҡиў«зғӯж°ҙзғ«гҖҒз”Ёжү“зҒ«жңәзғ§пјҢжҲ–йҒӯеҲ°еҗ„з§Қж–№ејҸзҡ„ж®ҙжү“гҖӮ
гҖҖгҖҖеҸҚдҫҰжҹҘжүӢж®өеңЁиҝӣе…Ҙз»„з»Үзҡ„йӮЈдёҖеҲ»е·Із»Ҹз”ЁдёҠдәҶгҖӮе®үж¬ЎеҢәдёҖеҗҚж°‘иӯҰйҖҸйңІпјҢеҸӘиҰҒиў«йӘ—е…ҘеҶң家йҷўпјҢжҜҸдәәзҡ„жүӢжңәгҖҒиә«д»ҪиҜҒйғҪе°Ҷ被没收пјҢвҖңдёҠзә§вҖқ规е®ҡдёҚиғҪе‘ҠиҜүеҲ«дәәзңҹеҗҚпјҢзӣёдә’д№Ӣй—ҙеҸӘиғҪз§°е‘јеҢ–еҗҚгҖӮ
гҖҖгҖҖеҗҢж—¶пјҢжҜҸеҚҠдёӘжңҲе·ҰеҸіпјҢдј й”Җз»„з»Үдјҡе°ҶжҜҸдёӘеҶң家йҷўзҡ„дәәе‘ҳи°ғж•ҙпјҢеҠ йҖҹдәәе‘ҳжөҒеҠЁпјҢзЎ®дҝқеҗҢдёҖеҜқе®Өзҡ„дәәзӣёдә’йҡҫд»ҘзҶҹжӮүгҖӮ
гҖҖгҖҖ银иЎҢеҚЎд№ҹиў«еҠЁдәҶжүӢи„ҡпјҢеүҚиҝ°ж°‘иӯҰиҜҙпјҢжңүзҡ„вҖңеӨҙзӣ®вҖқдјҡйҡҸжңәйҖүжӢ©ж•°еҗҚжҲҗе‘ҳпјҢи®©е…¶е‘ҠиҜү银иЎҢеҜҶз ҒпјҢд№ӢеҗҺиҝҷдәӣеҚЎиў«з”ЁдәҺдј й”Җдәәе‘ҳиҙӯд№°дә§е“ҒгҖҒзӣёдә’иҪ¬иҙҰгҖӮ
гҖҖгҖҖиҝҷдәӣж–№жі•жөҒдј дәҺеҗ„ең°пјҢдёҚз”ЁеҶҚйҮҚж–°вҖңеҸ‘жҳҺвҖқгҖӮеҠһжЎҲдәәе‘ҳиҜҙпјҢжӯӨж¬ЎжҠ“иҺ·зҡ„дёҖеҗҚеҘіз”ҹпјҢдёӘеӯҗеЁҮе°ҸпјҢдёҖи„ёеҚ•зәҜпјҢдҪҶеҚҙжҳҜдј й”Җз»„з»ҮдёҖеҗҚжңҖй«ҳзӯүзә§зҡ„вҖңдёҖзә§еӨҙзӣ®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ёҚе°‘жҲҗе‘ҳйғҪиҜ•еӣҫжҸҗеҚҮиҮӘе·ұзҡ„зӯүзә§гҖӮжҢүз…§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зҡ„规е®ҡпјҢвҖңдёҖзә§еӨҙзӣ®вҖқдёҚжҳҜеӣәе®ҡзҡ„пјҢдёҖж—ҰдёӢзәҝиҫҫеҲ°дёҖе®ҡзҡ„вҖңдёҡз»©вҖқпјҢж–°зҡ„вҖңдёҖзә§еӨҙзӣ®вҖқе°ұиҜһз”ҹдәҶгҖӮиҖҢеҪ“зҶ¬еҲ°вҖңдёҖзә§еӨҙзӣ®вҖқпјҢдҫҝеҸҜдёҚеңЁе»ҠеқҠз”ҹжҙ»пјҢеҸӘйңҖиҰҒйҖҡиҝҮзҪ‘з»ңгҖҒз”өиҜқдҪңдёҖдәӣеҶізӯ–пјҢжҜ”еҰӮжҙ—и„‘гҖҒ收е…Ҙж–№ејҸжҲ–зӘқзӮ№йҖүеқҖгҖӮ
гҖҖгҖҖзӣёиҫғиҖҢиЁҖпјҢвҖңдәҢзә§еӨҙзӣ®вҖқеҝ…йЎ»еңЁе»ҠеқҠз”ҹжҙ»пјҢжӣҙдҪҺеұӮзә§зҡ„вҖңдёүзә§еӨҙзӣ®вҖқйңҖиҰҒж—¶еҲ»зӣ‘зқЈдҪҺеұӮдј й”Җдәәе‘ҳпјҢз»ҸеёёеҺ»еҗ„еҶң家йҷўиҪ¬иҪ¬гҖӮ
гҖҖгҖҖжҚһеӣһжҲҗжң¬пјҢиөҡй’ұпјҢз”ҡиҮіе®һзҺ°вҖңиҮӘжҲ‘д»·еҖјвҖқвҖ”вҖ”иҝҷжҲҗдёәдёҚе°‘дәәж·ұйҷ·дј й”Җзҡ„зҗҶз”ұгҖӮ
гҖҖгҖҖеҠһжЎҲж°‘иӯҰе‘ҠиҜүи®°иҖ…пјҢе…¶е®һпјҢдёҚе°‘дәәйғҪзҹҘйҒ“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йӘ—еұҖпјҢдҪҶеӨҡеҗҚе«Ңз–‘дәәи°ҲеҲ°дәҶдёҖдёӘжҷ®йҒҚеҝғжҖҒпјҡдёҚз”ҳеҝғеҠЁиҫ„еҚҒеҮ дёҮе…ғжү“дәҶж°ҙжјӮпјҢвҖңиҖҢе”ҜдёҖжҚһеӣһй’ұзҡ„ж–№жі•пјҢжҳҜжҠ•е…ҘжӣҙеӨҡй’ұпјҢеҸ‘еұ•жӣҙеӨҡдёӢзәҝпјҢж…ўж…ўеңЁз»„з»ҮйҮҢжҲҗдёәйўҶеҜјпјҢиөҡе…¶д»–дәәзҡ„й’ұ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ҘеҫҖжһҒе°‘и®Өе®ҡзҡ„зҪӘеҗҚ
гҖҖгҖҖ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дј й”Җз»„з»Ү2017е№ҙ3жңҲеҸ‘з”ҹзҡ„дёҖжЎ©еҲ‘дәӢжЎҲ件пјҢеҠ йҖҹдәҶе®ғзҡ„иҰҶзҒӯгҖӮ
гҖҖгҖҖеҪјж—¶пјҢ1993е№ҙеҮәз”ҹзҡ„еӨ§еӯҰз”ҹйӮұжҹҗиў«еҗҢеӯҰд»ҘжұӮиҒҢзҡ„еҗҚд№үйӘ—е…ҘдәҶ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зӘқзӮ№гҖӮеңЁе®үж¬ЎеҢәжқЁзЁҺеҠЎд№Ўе’Ңе№іжқ‘зҡ„дёҖеӨ„еҮәз§ҹйҷўйҮҢпјҢдј й”ҖжҲҗе‘ҳиҰҒжұӮйӮұжҹҗе…ҘдјҷпјҢйӮұжҹҗе§Ӣз»ҲдёҚд»ҺгҖӮ
гҖҖгҖҖеӨҡеҗҚдј й”Җдәәе‘ҳйҡҸеҗҺеҫҖйӮұжҹҗеҳҙйҮҢзҒҢж°ҙпјҢеҮ зў—ж°ҙдёӢеҺ»пјҢйӮұжҹҗдёҖеҠЁдёҚеҠЁдәҶгҖӮжі•еҢ»йүҙе®ҡпјҢйӮұжҹҗзі»з”ҹеүҚйўҲйғЁеҸ—жүјеҺӢеҸҠејӮзү©пјҲиғғеҶ…е®№зү©пјүеҗёе…ҘиҮҙжңәжў°жҖ§зӘ’жҒҜжӯ»дәЎгҖӮ
гҖҖгҖҖеҪ“е№ҙ12жңҲпјҢе»ҠеқҠдёӯйҷўдёҖе®ЎеҲӨеҶіеӨҡеҗҚдј й”Җдәәе‘ҳзҠҜж•…ж„ҸдјӨе®ізҪӘгҖҒйқһжі•жӢҳзҰҒзҪӘпјҢеҲҶиҺ·жңүжңҹеҫ’еҲ‘2е№ҙ6дёӘжңҲиҮі15е№ҙдёҚзӯүгҖӮжІіеҢ—й«ҳйҷўжӯӨеҗҺз»ҙжҢҒеҺҹеҲӨгҖӮ
гҖҖгҖҖиҖҢеңЁеӨ©жҙҘпјҢеӨ§еӯҰз”ҹжқҺж–Үжҳҹ2017е№ҙ7жңҲеӣ иҜҜе…Ҙ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иҖҢж„ҸеӨ–жӯ»дәЎзҡ„дәӢ件пјҢдәҰеј•иө·иҲҶи®әе…іжіЁгҖӮ
гҖҖгҖҖе®үж¬ЎеҢәжЈҖеҜҹйҷўеҠһжЎҲжЈҖеҜҹе®ҳе‘ҠиҜүдёӯеӣҪйқ’е№ҙжҠҘВ·дёӯйқ’еңЁзәҝи®°иҖ…пјҢ他们з»ҸиҝҮжўізҗҶеҸ‘зҺ°пјҢе®һйҷ…дёҠпјҢ2013е№ҙејҖе§ӢпјҢиҫ–еҢәеҶ…йҷҶз»ӯжңү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зҡ„зӣёе…іжЎҲ件еҮәзҺ°пјҢеёёи§Ғж¶үе«ҢзҪӘеҗҚжҳҜйқһжі•жӢҳзҰҒгҖҒжҠўеҠ«зӯүпјҢжЁЎејҸеҸҠз»„з»Үжһ¶жһ„еҚҒеҲҶеӣәе®ҡпјҢз”ҡиҮіпјҢдёҖдәӣжЎҲ件дёӯзҡ„еҗҚеӯ—пјҢеңЁеҸҰдёҖдёӘжЎҲ件йҮҢд№ҹеҮәзҺ°иҝҮгҖӮ
гҖҖгҖҖиҝҷеј•иө·дәҶе®үж¬ЎеҢәжңүе…ійғЁй—Ёзҡ„е…іжіЁгҖӮйҡҸеҗҺпјҢ他们жұҮжҖ»дәҶдёҺвҖңиқ¶иҙқи•ҫвҖқжңүе…ізҡ„жүҖжңүиЎҢж”ҝиҝқжі•гҖҒеҲ‘дәӢжЎҲ件иө„ж–ҷпјҢиҜ•еӣҫжўізҗҶжҜҸеҗҚдј й”Җдәәе‘ҳд№Ӣй—ҙзҡ„иҒ”зі»пјҢжңҖз»ҲжҺҢжҸЎдәҶдёүзә§д»ҘдёҠдј й”ҖеӨҙзӣ®зҡ„еӨ§иҮҙи„үз»ңеӣҫгҖӮ
гҖҖгҖҖиў«е‘Ҡдәәеұұж–Ңжһ—жңҖе…ҲеҮәзҺ°еңЁж”ҝжі•йғЁй—Ёзҡ„и„үз»ңеӣҫдёҠгҖӮеңЁеӨ§еӯҰз”ҹйӮұжҹҗжӯ»дәЎжЎҲ件дёӯпјҢдёҖеҗҚзҪӘзҠҜдҫӣиҝ°з§°пјҢиҮӘе·ұжҳҜвҖңдёүзә§еӨҙзӣ®вҖқеұұж–Ңжһ—зҡ„дёӢзәҝгҖӮд»Һеұұж–Ңжһ—е…ҘжүӢпјҢеҠһжЎҲж°‘иӯҰйҷҶз»ӯеҸҲеҸ‘зҺ°дәҶеҗҙзҷҫжңүгҖҒжҪҳжҳҺжҳҺзӯүдәә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дёҖдёӘвҖҳдәҢзә§еӨҙзӣ®вҖҷдёҚзҹҘйҒ“дёҠзәҝзҡ„зңҹеҗҚпјҢдёҖж®өж—¶й—ҙжЎҲ件еғөжҢҒдҪҸдәҶпјҢеҗҺжқҘпјҢжҲ‘们еңЁд»–зҡ„ж”Ҝд»ҳиҪҜ件дёҠжүҫеҲ°дәҶзәҝзҙўгҖӮвҖқиҜҘж°‘иӯҰиҜҙпјҢд»–еҸ‘зҺ°пјҢдёҖжқЎж”Ҝд»ҳи®°еҪ•дёҠзҡ„ж•°еӯ—жҳҜ2900зҡ„еҖҚж•°гҖӮ
гҖҖгҖҖж•Ҹж„ҹзҡ„ж°‘иӯҰйЎәи—Өж‘ёз“ңпјҢжһң然пјҢеҜ№ж–№жҳҜд»ҘеҫҖдј й”ҖжЎҲ件дёӯйҡҫд»ҘжҹҘиҺ·зҡ„вҖңдёҖзә§еӨҙзӣ®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е«Ңз–‘дәәйҷҶз»ӯеҪ’жЎҲгҖӮйҷҲжҳҺйңһйӮЈж—¶е·ІзҰ»ејҖз»„з»ҮпјҢеӣһеҲ°жӯЈеёёз”ҹжҙ»пјҢиҖҢжңүзҡ„дәәеңЁйӮұжҹҗжӯ»дәЎд№ӢеҗҺиәІеҲ°еӨ–ең°йҒҝйЈҺеӨҙпјҢи§ҒеҲ°е»ҠеқҠж°‘иӯҰпјҢеҸҚиҖҢиҲ’дәҶдёҖеҸЈж°”пјҡвҖңдҪ 们з»ҲдәҺжқҘдәҶгҖӮвҖқ
гҖҖгҖҖеҠһжЎҲжЈҖеҜҹе®ҳеҜ№и®°иҖ…еҲҶжһҗпјҢдёҺд»ҘеҫҖжЎҲ件зҡ„жҳҫи‘—дёҚеҗҢпјҢеңЁдәҺжӯӨж¬ЎжЎҲ件иө·иҜүзҪӘеҗҚеҢ…жӢ¬ж¶үе«Ңз»„з»ҮгҖҒйўҶеҜјдј й”Җжҙ»еҠЁзҪӘгҖӮжҢүз…§жі•еҫӢ规е®ҡпјҢиҝҷдёӘзҪӘеҗҚиҰҒжұӮе«Ңз–‘дәәиҮіе°‘жҳҜвҖңдёүзә§еӨҙзӣ®вҖқпјҢдё”з»„з»ҮеҢ…еҗ«30еҗҚд»ҘдёҠзҡ„жҲҗе‘ҳ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жҖҺд№ҲиҜҒжҳҺжңү30еҗҚд»ҘдёҠзҡ„жҲҗе‘ҳпјҹеҫ—жңүзӣёе…іиҜҒдәәиҜҒиЁҖпјҢ并且иғҪе’Ңзӣёе…ід№ҰиҜҒзӯүиҜҒжҚ®еҪўжҲҗиҜҒжҚ®й“ҫгҖӮвҖқжЈҖеҜҹе®ҳиЎЁзӨәпјҢдҪҶжҳҜпјҢдёҖдәӣдј й”ҖжҲҗе‘ҳеҸҚдҫҰжҹҘиғҪеҠӣејәпјҢиҖҢдё”дәәе‘ҳжөҒеҠЁеӨ§пјҢжңүж—¶еҫҲйҡҫзЎ®и®ӨеҪјжӯӨзңҹе®һиә«д»ҪгҖӮдёҖж—ҰеҮәдәӢпјҢ他们常дјҡе…ҲиәІеҲ°е°Ҹж ‘жһ—пјҢиҝҷз»ҷеҸ–иҜҒгҖҒи®Ҝй—®йғҪеёҰжқҘеӣ°йҡҫгҖӮ
гҖҖгҖҖжЈҖеҜҹе®ҳиҜҙпјҢиҝҷж¬ЎпјҢе®үж¬ЎеҢәзӣёе…ійғЁй—Ёе·ҘдҪңеҠӣеәҰеҫҲеӨ§пјҢжңҖеҗҺд»Ҙж¶үе«ҢиҜҘзҪӘиө·иҜүпјҢвҖңзЎ®е®һжҳҜдёҖдёӘзӘҒз ҙ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 еӨҡйғЁй—Ёз»јеҗҲжІ»зҗҶ
гҖҖгҖҖ2018е№ҙ12жңҲ4ж—ҘпјҢе®үж¬ЎеҢәжі•йҷўдҪңеҮәдёҖе®ЎеҲӨеҶіпјҢи®Өе®ҡеұұж–Ңжһ—гҖҒеҗҙзҷҫжңүгҖҒжҪҳжҳҺжҳҺгҖҒйҷҲжҳҺйңһдәҺ2014е№ҙе№ҙеҲқиҮі2017е№ҙ3жңҲеңЁе®үж¬ЎеҢәжқЁзЁҺеҠЎд№Ўз»„з»ҮгҖҒйўҶеҜјдј й”Җжҙ»еҠЁпјҢеј•иҜұгҖҒиғҒиҝ«еҸӮеҠ иҖ…继з»ӯеҸ‘еұ•д»–дәәеҸӮеҠ пјҢйӘ—еҸ–иҙўзү©пјҢжһ„жҲҗз»„з»ҮгҖҒйўҶеҜјдј й”Җжҙ»еҠЁзҪӘзӯү3йЎ№зҪӘеҗҚгҖӮ
гҖҖгҖҖе…¶дёӯпјҢеҜ№дәҺз»„з»ҮгҖҒйўҶеҜјдј й”Җжҙ»еҠЁзҪӘпјҢ4еҗҚиў«е‘ҠдәәеҸҠе…¶иҫ©жҠӨеҫӢеёҲеңЁе®ҡзҪӘж–№йқўеқҮж— ејӮи®®пјҢйҷҲжҳҺйңһзӯүдәәзҡ„еҫӢеёҲеҲҷжҸҗеҮәеҪ“дәӢдәәжңүеҸ—дәәеј•иҜұж¬әйӘ—гҖҒе·Іи„ұзҰ»з»„з»Үзӯүжғ…иҠӮпјҢе»әи®®йҮҸеҲ‘ж—¶дәҲд»ҘиҖғиҷ‘гҖӮ
гҖҖгҖҖиҜҘйҷўеҲ‘дәӢе®ЎеҲӨеәӯеәӯй•ҝеҲҳзЈҠе‘ҠиҜүдёӯеӣҪйқ’е№ҙжҠҘВ·дёӯйқ’еңЁзәҝи®°иҖ…пјҢд»ҘеҫҖдј й”ҖжЎҲ件зҡ„иў«е‘ҠдәәеӨҡжҳҜз»„з»Үзҡ„дҪҺеұӮдәәе‘ҳпјҢеӨҡжһ„жҲҗйқһжі•жӢҳзҰҒзҪӘгҖҒжҠўеҠ«зҪӘзӯүпјҢиғҪжһ„жҲҗвҖңз»„з»ҮгҖҒйўҶеҜјдј й”Җжҙ»еҠЁзҪӘвҖқзҡ„й«ҳзә§еҲ«жҲҗе‘ҳеҫҲе°‘пјҢиҖҢиҜҘжЎҲзҡ„иҜҒжҚ®иҫҫеҲ°дәҶзӣёе…іе®ҡзҪӘж ҮеҮҶгҖӮ
гҖҖгҖҖжЎҲ件дёҖе®Ўе‘ҠдёҖж®өиҗҪпјҢдёҚиҝҮпјҢеңЁе®үж¬ЎеҢәж”ҝ法委жңүе…іиҙҹиҙЈдәәзңӢжқҘпјҢиҝҷзҰ»жңҖзҗҶжғізҡ„еұҖйқўд»Қе·®вҖңжңҖеҗҺдёҖе…¬йҮҢ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ёәдәҶи§Јж•‘еҸ—йӘ—еӨ§еӯҰз”ҹпјҢиҝҷеҗҚиҙҹиҙЈдәәжӣҫдәІиөҙвҖңжү“дј вҖқеүҚзәҝгҖӮд»–дёҺеҸ—йӘ—иҖ…и°ҲдәҶдёҖжҷҡдёҠпјҢ第дәҢеӨ©пјҢдёҖйғЁеҲҶеӨ§еӯҰз”ҹжүҚиҒ”зі»дәҶ家йҮҢпјҢжңүзҡ„еҲҷжҺЁз§°иҖҒ家жқ‘йҮҢжІЎз”өиҜқпјҢвҖңжң¬жқҘжңҖзҗҶжғізҡ„еұҖйқўпјҢжҳҜи§Јж•‘ж—¶жүҖжңүдәәйғҪиғҪжңү家йҮҢиҒ”系他们пјҢжҠҠ他们жҺҘеӣһ家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жңҖз»ҲпјҢ家йҮҢиғҪжҺҘзҡ„жҜ•дёҡз”ҹпјҢжҺҘеӣһеҺ»дәҶпјӣдёҚиғҪжҺҘзҡ„пјҢеҸ—йӘ—иҖ…иҮӘе·ұд№°зҘЁеӣһ家дәҶпјӣе®һеңЁжІЎй’ұпјҢе®үж¬ЎеҢәжү“еҮ»дј й”ҖеҠһе…¬е®Өе…ҲеҮәй’ұд№°дәҶиҪҰзҘЁпјҢеҶҚжҠҠж—¶й—ҙгҖҒиҪҰж¬Ўе‘ҠиҜүеҜ№ж–№е®¶йҮҢгҖӮ
гҖҖгҖҖдёҖдәӣеҸ—йӘ—еӨ§еӯҰз”ҹдёҚж„ҝеӣһ家зҡ„зҗҶз”ұпјҢд»Өдәәе”Ҹеҳҳпјҡжңүзҡ„дәәжІүжІҰдәҺз”·еҘіж··дҪҸпјҢдёҚж„ҝеӣһеҪ’жӯЈеёёз”ҹжҙ»пјӣжңүзҡ„дәә家еўғиҙ«еҜ’пјҢ2900е…ғеҜ№е…¶еҲҶйҮҸеҫҲйҮҚпјҢжҖ»жҳҜдёҚз”ҳеҝғпјӣжңүзҡ„дәәеҒҡзқҖеҸ‘иҙўжўҰпјҢжғіз»§з»ӯеқ‘е®іеҲ«дәәгҖӮеүҚиҝ°иҙҹиҙЈдәәе°ҶжӯӨй—®йўҳжҖ»з»“дёәвҖңжү“иҖҢдёҚж•ЈпјҢйҒЈиҖҢдёҚиҝ”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жҜҸеҪ“иҝҷж—¶пјҢе®үж¬ЎеҢәеёӮеңәзӣ‘зқЈз®ЎзҗҶеұҖжү“дј дёӯйҳҹйҳҹй•ҝжӯҰж–Ңеёёи·ҹеҸ—йӘ—иҖ…и°ҲеҝғпјҢвҖңжҲ‘и·ҹ他们иҜҙпјҢдҪ еҺ»жү“е·ҘпјҢиғҪиөҡдёүеӣӣеҚғе…ғпјҢдҪ еңЁиҝҷеҫ…дёҖдёӘжңҲпјҢеҸҚиҖҢиҰҒжҺҸй’ұпјҢеҗғзҡ„иҝҳеҫҲи„ҸпјҢеҚҒеҮ дёӘдәәдҪҸдёҖдёӘеұӢеӯҗпјҢз”ҡиҮідёҚи®©дҪ еҮәеҺ»гҖӮеҰӮжһңжӯЈеёёжү“е·ҘпјҢиӮҜе®ҡдёҚдјҡиў«йҷҗеҲ¶иҮӘз”ұ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дәәдёҚеҸҜиғҪдёҖеӨңжҡҙеҜҢгҖӮвҖқжӯҰж–ҢиҜҙпјҢи°Ҳеҝғеҹәжң¬жҳҜвҖңдёҖеҜ№дёҖвҖқиҝӣиЎҢпјҢеҗҰеҲҷдәәдёҖеӨҡпјҢеҸ—йӘ—иҖ…е°ұеҸҜиғҪеҗ¬дёҚиҝӣеҺ»гҖӮдёҖдёӘзӘқзӮ№еҚҒеҮ дәәпјҢжңүж—¶дёҠеҚҲи§Јж•‘пјҢиҰҒеҲ°дёӢеҚҲжҲ–жҷҡдёҠжүҚиғҪжҢЁдёӘи°Ҳе®ҢгҖӮ
гҖҖгҖҖд»Ҡе№ҙзҡ„жғ…еҶөе·ІеҘҪдәҶдёҚе°‘гҖӮеӨҡеҗҚеҸ—и®ҝдәәеЈ«еӣһеҝҶпјҢиҝҮеҺ»пјҢдёҖдәӣеҸ—йӘ—иҖ…и®Өдёәи§Јж•‘дәәе‘ҳжҳҜвҖңз ёдәҶд»–зҡ„з”ҹж„ҸвҖқпјҢз”ҡиҮіиҜҙи§Јж•‘дәәе‘ҳжүҚжҳҜйӘ—еӯҗпјҢжңүзҡ„еҸ—йӘ—иҖ…еҲҷеҳҙдёҠиҜҙдёҚеҒҡдәҶпјҢд№ҹзңӢзқҖд»–дёҠзҒ«иҪҰдәҶпјҢдҪҶеҚҠи·ҜеҚҙеҸҲжҠҳиҝ”еӣһжқҘгҖӮ
гҖҖгҖҖдәӢе®һдёҠпјҢйқўеҜ№дј й”ҖпјҢе®үж¬ЎеҢәе·ІйҮҮеҸ–дәҶдёҖзі»еҲ—иЎҢеҠЁгҖӮе®үж¬ЎеҢәеёӮеңәзӣ‘зқЈз®ЎзҗҶеұҖзЁҪжҹҘеұҖеұҖй•ҝзҺӢзҺүжұҹд»Ӣз»ҚпјҢиҜҘеҢәжҠҪи°ғдәҶе…¬е®үгҖҒеёӮеңәзӣ‘зқЈз®ЎзҗҶеұҖзӯүйғЁй—ЁеҠӣйҮҸпјҢжҲҗз«ӢдәҶдёҖеҸӘдё“й—Ёзҡ„жү“дј йҳҹдјҚпјҢ并组з»Үе°ҸеҢәгҖҒжқ‘еә„иҝӣиЎҢеҸҚдј й”Җзҡ„еӨ§йҮҸе®Јдј 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Јдј дәҶзҫӨдј—е°ұзҹҘйҒ“пјҢдј й”Җдәәе‘ҳе’Ңжҷ®йҖҡдәәжңүдёҚдёҖж ·зҡ„дёҫеҠЁгҖӮзәҝзҙўд№ҹдјҡеҸҠж—¶е‘ҠиҜүзӣёе…ійғЁй—ЁгҖӮвҖқжӯҰж–ҢеҲҶжһҗпјҢжҜ”еҰӮпјҢеӨҡжҳҜзҫӨеұ…пјҢдёҖдёӘеұӢеӯҗдҪҸеҚҒеҮ дёӘдәәпјҢиҖҢеҪ“ең°жҷ®йҖҡз§ҹжҲҝйҖҡеёёжҳҜдёҖдёӨдәәжҲ–дёҖ家дәәдҪҸпјӣе’ҢдәәиҒҠеӨ©иҜҙиҜқпјҢе–ңж¬ўд»Ӣз»ҚжүҖи°“дә§е“ҒпјҢзңјзҘһе’ҢдёҫеҠЁд№ҹдёҺеёёдәәдёҚеҗҢгҖӮ
гҖҖгҖҖдҝқжҠӨе№ҙиҪ»дәәжӣҙжҲҗдәҶеҚҒеҲҶиҰҒзҙ§зҡ„дәӢжғ…гҖӮе®үж¬ЎеҢәж”ҝ法委жңүе…іиҙҹиҙЈдәәеҜ№и®°иҖ…иҜҙпјҢе®үж¬ЎеҢәиҫ–еҢәйӣҶдёӯдәҶе»ҠеқҠеёӮеӨҡжүҖй«ҳж ЎпјҢдёәжӯӨпјҢ他们组з»ҮеӨ§йҮҸдәәеҠӣиҝӣй«ҳж Ўе®Јдј пјҢжҸҗзӨәжҜ•дёҡз”ҹиҺ«иҜҜе…Ҙдј й”ҖпјҢжҠҠйў„йҳІй’Ҳжү“еңЁеӯҰз”ҹиө°еҮәж Ўй—Ёд№ӢеүҚгҖӮ